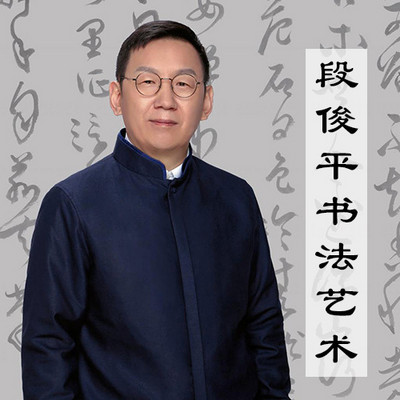节目简介
# 乾隆皇帝书画收藏癖好
# 盖章狂人乾隆外号来源
# 乾隆文物破坏者争议
# 乾隆书画题跋行为
# 故宫藏附冲三巨图
#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
# 唐代五牛图乾隆印章
# 乾隆书画印章数量
# 附冲三巨图赝品争议
# 乾隆文物管理评价
乾隆皇帝因其在书画作品上大量盖章和题跋的行为,被称为“盖章狂人”。这一外号源于他对故宫藏《附冲三巨图》等作品的极端处理:他不仅在赝品《附冲三巨图》上盖印五十多枚,还命臣子填满画面空白,导致原画美感严重受损。
其“文物破坏者”的争议进一步体现在对王羲之作品的过度干预中。例如,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被乾隆加盖一百七十二枚印章,并在折缝处题写“神”字;《中秋帖》仅二十二字,却被盖印八十余枚,远超原作篇幅。
此外,唐代《五牛图》等经典画作也难逃乾隆的“书画印章”狂热。他在《五牛图》上加盖数十枚印章,削弱了原画的乡土气息;明代《人奇图卷》和《勤用墨画》分别被盖印十四枚及三十余枚,进一步引发对其文物管理方式的批评。
这些行为不仅反映了乾隆对收藏的痴迷,也暴露了其“赝品鉴定”能力的不足,如将赝品误作真迹题跋。后世对其“历史评价”多聚焦于艺术保护与破坏的双重性,成为研究清代文物管理的重要案例。
评论
还没有评论哦
该专辑其他节目
- 394、没有唐太宗,王羲之还是书圣吗?
- 395、猜猜东床快婿与哪个书法有关?
- 396、二王的书法特点与比较
- 390、为什么这次没有名气的书法作品竞拍了2.5亿
- 391、历史这两位竟敢褒贬王羲之
- 392、书法作品的六个美学特征是什么?
- 393、古代书法家对万物的书写雅称
- 385、乾隆皇帝的书法为什么是肥厚圆润
- 386、由于乾隆皇帝喜欢,他的书法才得以挽救
- 387、乾隆皇帝与他书法赵孟頫的书法差距
- 388、乾隆皇帝的书法市场行情
- 389、乾隆皇帝有个外号猜猜看
- 382、乾隆皇帝的书法老师是谁?
- 383、乾隆皇帝受谁的书法影响最大?
- 380、跟当代老师学书法主要学什么?
- 381、学五体书法字帖大集锦
- 378、临帖不是只临形
- 379、当代书法太偏重于展厅的结果是什么?
- 377、练书法的终极解药,破壁五式
- 375、拜书法老师时一定要问的三个问题
- 376、学习书法要避免的几个坑
- 372、专家说普通人看不懂书法
- 373、临帖如何选帖
- 374、学习书法越勤快越好吗?
- 371、当代书法已美学中毒
- 366、欣赏书法之从文镜到心境
- 367、王羲之为什么能成为书圣,看看孙过庭的描述
- 368、不要拿这个字来掩饰自己,没有书法基本功的事实
- 369、练习书法避免的几个坑
- 370、倡导丑书的有一块遮羞布
回到顶部
/
收听历史
清空列表